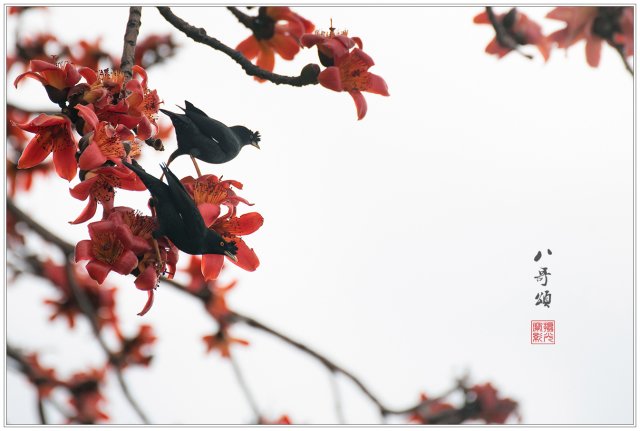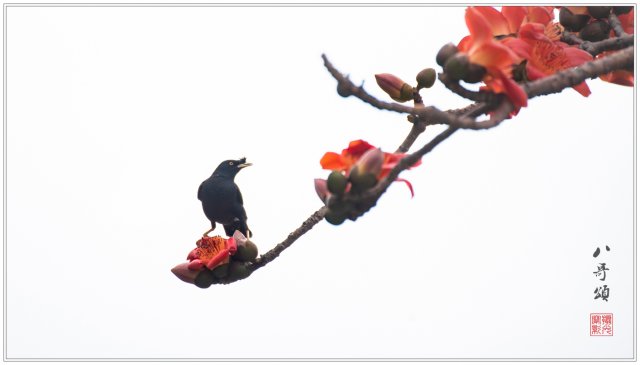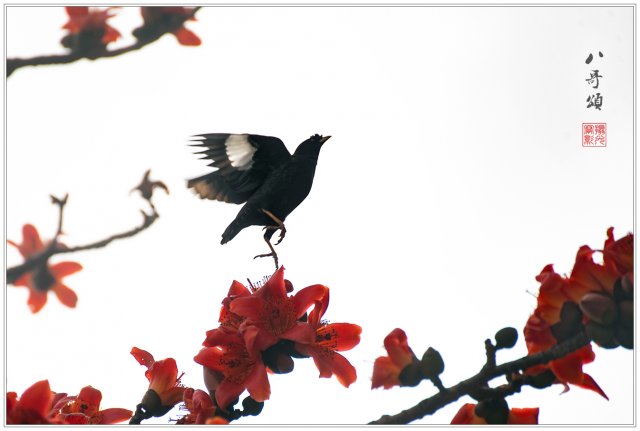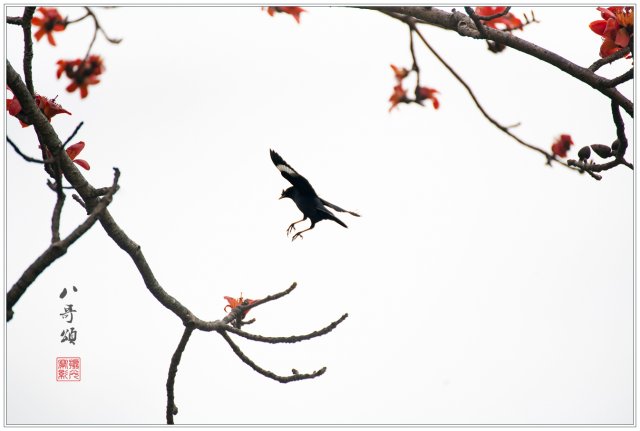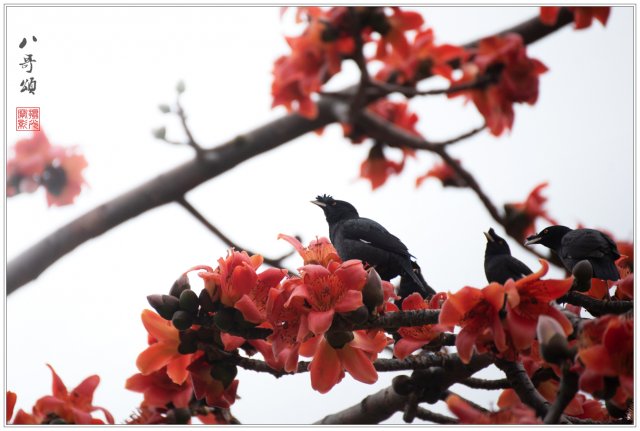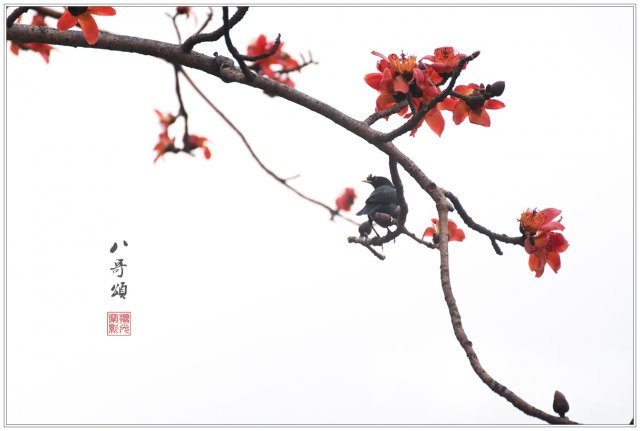進退之間 @ 草根散記 ─ 2021/04/26
春天,飛鵝山上濃霧掩蓋,前後左右白茫茫。一片朦朧之中,天空傳來陣陣小型馬達的聲音。見路旁有人手持遙控器,便隨口一問。
「過了雲層嗎?」
「過了。」
「有多高?」
「大概五十米吧。」
沒錯,就只是五十米的差別,他拍到是是雲海,我看到的是 A4 濃霧。
航拍機一升空,熟悉的老地方,頓然變為前所未見。航拍不單只為拍攝者帶來全新的視角,亦彷彿將攝影技藝提昇到嶄新的高度。須知道,現今的航拍機,可說是集合攝影與人工智能科技之大成。好些先進的型號,差不多是只要把它拋到空中,就可以拍出令人讚嘆不已的畫面。隨之而來,在社交媒體吸納大量的 Like,不在話下。
回顧歷史,科技進步,為攝影帶來不少改變。N 年前,全自動曝光 P 模式面世,廠家的宣傳口號是:你只要對焦,其餘的交給相機辦。於是,人們應對曝光的能力下降了。後來,自動對焦也有了,就變成「你只需要構圖」。於是,手動對焦技巧以及靈活的景深運用幾成絕技。曾幾何時,拍完一卷幻燈片,是滿有信心地等待沖印的結果。如今,可會拍上數十幅也不回看機背 LCD?
事實告訴我們,即使有了自動曝光,攝影者仍舊需要認識曝光;有了自動對焦,又快又準之餘,亦要求我們掌握新的一套對焦技巧。至於機背 LCD,除了檢視影像之外,還要看懂亮度分佈圖。
人類進化,尾巴不見了,身上再沒有厚厚的皮毛。然而這進化,同時是平衡及禦寒能力的退化。是進還昰退?視乎觀點與角度。航拍面世,不知又會為攝影帶來哪方面的進,哪方面的退?而進退之間,又是否能夠去蕪存菁?